「七一」又到了。7月1日是回歸日,象徵了香港殖民時期的終點,也標誌了在中國主權下特別行政區的起點,但每年重訪這個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日子,意義何在呢?
對國家主權來說,這當然是以盛大儀式宣示的機會,對本港親北京陣營者亦然;對於反對派,這當然是抗議日,甚至有人認為,是香港「現狀」大變、禮崩樂壞之始。
這個日子有另一層意義,較少有人注意。如果把時鐘撥回到1997年6月30日,那是「過渡期」的終結。我們今天都幾乎忘記了「過渡期」這個詞了,它在1980至90年代曾經是政治關鍵詞。1997年7月1日之後,不再過渡,「過渡」似乎便不再有意義了。而我卻想做一個思想實驗:我們不妨把當下香港再次想像為「過渡」。
過渡期想像比「2047」更貼近現實
在我解釋這個想法之前,我們不妨回想一下,回歸前的過渡期是什麼?首先,當年是指所謂「香港政治前途」確定後至九七的時期,以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簽署之時開始,但又在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前。這段時期,有一個明確的起點及終點。這個過渡期有一個特點:香港人要開始及這樣過渡,並不是自己決定的,而是由中英兩國確立的,我們相當被動,被拋進這條政治軌跡。既無全民公投,也無革命起義建立政權,說成是被送上賊船有點過火,倒像王家衛《阿飛正傳》結尾,張國榮及劉德華跳上了不知開往何處的異地火車。
我今天提出再次想像的「過渡期」,它遠沒有之前的確定。所謂過渡,是比從前更不可知的旅程,起點不再是聯合聲明,而是那個曾經各方認受及假設的「現狀」,儘管詮釋不一,但大概有個共識:近年的政治爭議的起端,就是大家深深體會「現狀」大變。不只是反對派說的禮崩樂壞,甚至是建制派,也愛講中港融合或中國機遇,均指涉著一個早已變及不斷變的「現狀」。至於旅程的終點,它可以是憲制安排及地位完全不同的香港,可以是不同的社經制度。更不可知的,是新過渡期到底會多長。這一段旅程複雜,路徑與終點仍然爭持不斷,絕對不是當年中英爭吵有沒有「直通車」那樣簡單。不過,有一點是清晰,它與此前的過渡期不同,它是一個香港人要主導參與的過渡,不能再是完全被動的。
我以為,「過渡期」的再次想像,比起近年高談「2047」更貼近現實。首先,「2047」香港要自決公投也好,要獨立建國也好,都只是一廂情願。如果中國的政治狀況大變,不用到2047年香港也可以大變,若否,恐怕到了2047年也不會有大變。因為,《基本法》不會到了2047年便失效了,當中的「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,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,五十年不變」,那只是含糊的說法,既不涉香港憲政地位,也無關政制安排,更沒有說明五十年後如何(打岔一下,倒是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,按道理可以提出在香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)。既然人心思變,客觀政經環境在變,比較合理的說法是,香港進入邁向爭持不下的政治願景之中的過渡期,這個說法,我相信各黨各派也不至於有太大異議。
似新還舊的政局
我提出這個想法,不為玩文字遊戲,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回應當下層出不窮的「自決論」、「獨立論」等等,也為反思傳統泛民主流的「民主抗共」及「民主中國」。如今香港的政局,基本上是一個僵局,可是人心思變,變出了比之前複雜、宏大及遙遠的政治願景,但做起來似新還舊,喧鬧過後,靜下來的政治風景卻讓人感到萬變不離其宗。一時是最後一戰,一時又不過跟傳統泛民政黨一樣去找票箱爭席位。不少新興團體無論喊著什麼口號,又或在街頭做過什麼行動,大家也一窩蜂地參選,讓人看到的,似乎只是泛民陣營內部的勢力重新分配,最多只是美其名的世代交替,這些究竟與那遙遠的政治願景有什麼關係?坐下來一想,好像沒有。有人要把這些政治新爭議視之為為了選票的炒作,雖過於犬儒,但也不無道理。
用一種極為同情理解的態度去看,也許都是過渡期不得不為之舉。正因為如此,我們更需要去把這種全新的過渡期政治講清楚,指導實踐。現代政治裡對「過渡期」的想像,我想到兩個例子,也許可以讓我們借鏡一下。
兩個過渡的想像
提起過渡,我馬上想到托洛茨基1938年的「過渡綱領」。拉闊一點,歐洲馬克思主義自19世紀末開始的爭論,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過渡。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沒有聯合起來起義,或起義失敗(如1848年的歐洲革命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),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又有穩定跡象時,革命者如何在非革命時刻準備革命?如何與還未政治化的工人發展關係?要不要參與議會民主?
在一戰前後,有修正主義的社民路線,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路線之爭,而托洛茨基帶著先前的問題與答案,以及他的俄國革命經驗(當然包括被史太林(台譯史達林)排擠迫害的經驗),在二次大戰展開的時刻,舉起第四國際、列寧主義旗幟,提出接合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(所謂「最低限度綱領」)與社會主義革命(「最大限度綱領」),由「今天」的條件及意識出發,達到無產階級奪權。
如今我們當然會覺得,不只托洛茨基,甚至是當年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過分樂觀,總覺得世界恍如在革命前夜,難怪《國際歌》裡有「這是最後的鬥爭」一句。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分析及革命理論,令過渡論裡的革命意志及策略,帶有歷史必然性的預設及調子。這些對現代中國人應該不會太陌生:毛澤東提出「新民主主義時期」也是一種社會主義過渡,以至後來大躍進時的「窮過渡」,都是這種過渡論的極端。但歷史必然論式的過渡論,在二戰後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中漸漸消失,更不用說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了。
另一個過渡論例子,從經驗上可能更接近香港,即冷戰時的東歐異見知識分子,當中我比較熟悉也相當著名的是波蘭的米奇尼克(Adam Michnik)及捷克的哈維爾(Václav Havel)。
米氏一般被稱為「新漸進主義」代表人物,也是團結工會「自我克制運動」(self-limiting movement)的構想者之一。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,波蘭有「三月事件」。捷克的共黨領導杜布切(Alexander Dubček)決定要脫離蘇聯的控制,進行改革,建立「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」。杜要求波蘭共黨領導哥穆克(Władysław Gomułka)與他合作,卻遭拒絕。波蘭學生上街抗議要求改革,米氏是其中一位遭拘捕監禁的學生。出獄後不久,他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(KOR),並在1976年時寫下《新漸進主義》。
創造更好的今天,而非明天
大部分論者被「自我克制運動」吸引,強調反對運動的民間性、公民社會不同部門及階級的團結、實踐公民自由、體現不屈及尊嚴,以至非暴力手段。米氏倡導,社會先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及生活,卻不以推翻統治者為目標,亦不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。然而,他的「新漸進主義」中含有一種特別的過渡時間觀,卻多為人所忽略。他雖不用「過渡」,但卻用了「漸進」;我不懂波蘭語,不知「漸進」一詞在波蘭語的原意,但英文譯作evolution或evolving,即生物學上的「演化」,是一個漫長超越個體生命的過程,個體無法決定及確定目標。那麼,個體的行動基礎是什麼呢?他認為,所有理想應該以創造更好的今天,而不是更好的明天。
米氏這番說話,表面有點像「心靈雞湯」,實質是拉丁文Carpe diem(把握當下)的新詮釋,只有把它放回當時的處境,方能了解他的深意。1968年蘇聯派軍隊坦克入侵捷克,鎮壓了布拉格之春運動,整個東歐陣營的反對派知道,有強大蘇軍撐腰,要打敗東歐共黨是幾乎不可能的。但是,米氏認為,「不可能」不應變成反抗的絕望,或絕望式的反抗,而應該把希望放在當下。換一個說法,歷史必然性已沒有了,歷史目的不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還是「真民主」都不可想望,然而,希望卻近在咫尺。
在差不多同一時間,哈維爾寫下著名的《無權者的力量》,文中講及一位賣菜大叔的抉擇:是否該在自己店前掛出官方布條?布條上的官方口號是否體現自己心裡所思所想?真心提問、思考、表達及行動,是「活在磊落真誠」(living in truth)的力量之源。他所想像的反對運動,是在當下實踐自由、開放、真誠、團結信任,而與日益腐敗、道德墮落及犬儒的政權成為一鮮明對比。也許因為這樣,中共才會那麼那麼害怕講真話的人,同時要逼迫他們在電視鏡頭前撒謊認罪。因為,讓人「活」在謊言之中,是後極權體制最核心的手段,對統治者來說,這比「說」及「相信」謊言更重要。
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
在我看來,哈與米所代表的東歐反對派,提出了一種新的過渡意識,卻與意識形態相異的托洛茨基一樣強調「今天」的重要性。如今反對者沒有一套歷史唯物論可依靠,也沒有西方民主必勝的冷戰式信念,因而也無法確信暴政必亡(這一兩年香港網上青年的「支爆論」(中國崩潰論)我便覺得很莫名奇妙)。活在僵局中,去計較某個行為對推翻體制有沒有用,亦等於玄談。對行動的判準只有一個,就是「更好的今天」:是否令個體今天更自由,社會生活變得更有意義。
我們可以以此來重新思考許多香港爭議。例如,我們不必討論「建設民主中國」有沒有用,關鍵是支聯會、關注中國人權、勞工等等的團體、個人,以及他們的實踐,是否正在創造更大更好的公民社會空間;幾年前有人說「讓蝗蟲再飛一會」可以促進香港本土意識,有利抵抗中共,實現自主自治。我們其實無謂對那個「一會」產生什麼連鎖反應,對它想像或幻想太多,而是應該問,族群化的社會及意識是否我們要的?它讓我們今天的社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。當大家在爭議城邦、自決、獨立時,我們要問,這些運動是否在當下創造了更好的社群生活,而不是爭論那個不知或是否會或何時才到達的彼岸,或者是哪個路線才能嬴在起跑線上,最快最能夠到達終點。更根本的是,我們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。
所謂當下,是正在發生,也同樣是一個過渡,這過渡雖更難掌握,卻是每天在我們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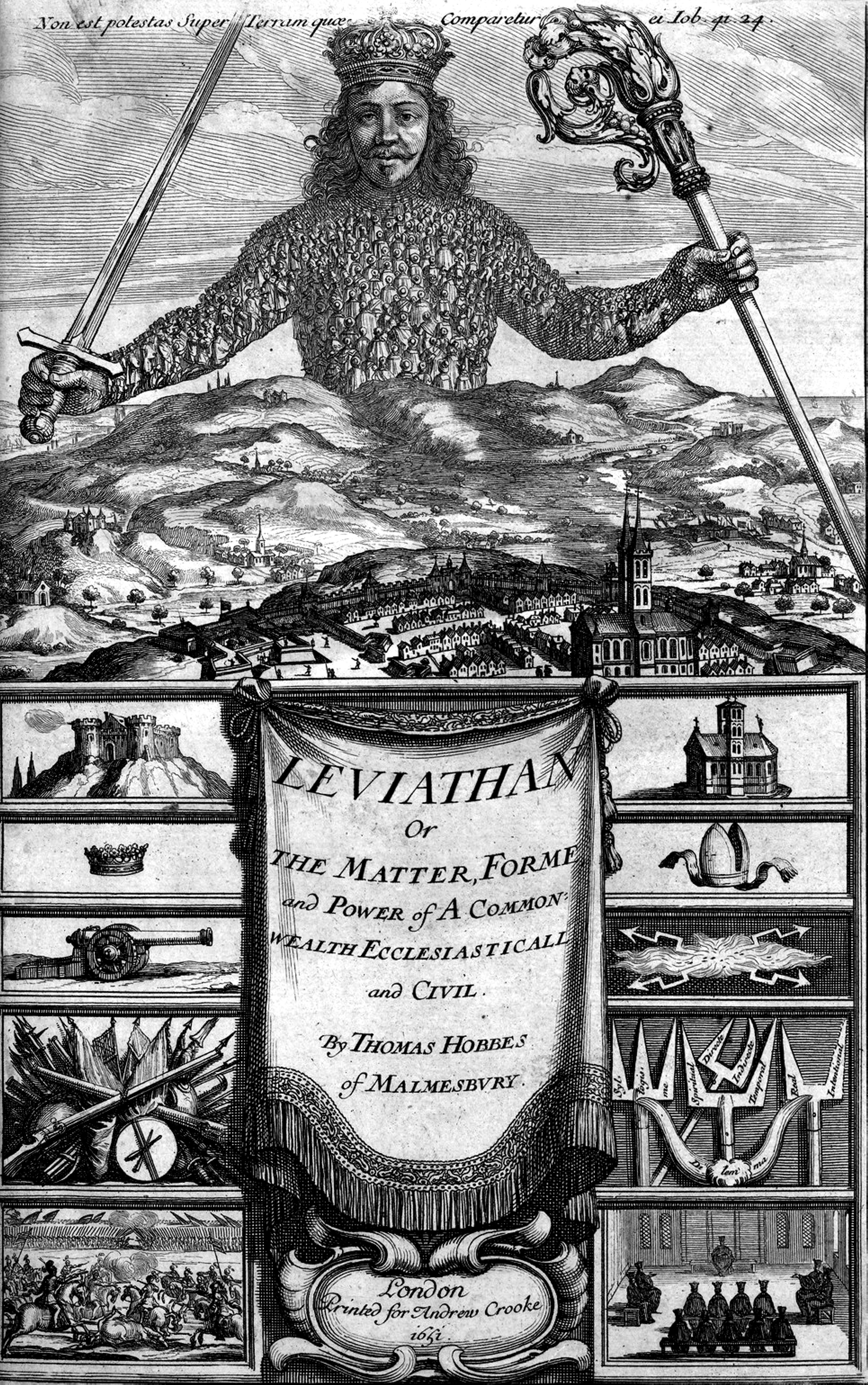 在盧梭的著作裡,政體是一個有規範意義的詞。”If scattered men, regardless of how many of them there may be, were successively enslaved to a single person, I see there nothing but a master and slaves; I do not see a people and its leader. It is, if you will, an aggregation, but not an association; there is neither public good nor body politic.” (The Social Contract, Chapter 5)
在盧梭的著作裡,政體是一個有規範意義的詞。”If scattered men, regardless of how many of them there may be, were successively enslaved to a single person, I see there nothing but a master and slaves; I do not see a people and its leader. It is, if you will, an aggregation, but not an association; there is neither public good nor body politic.” (The Social Contract, Chapter 5)



 漢語「忠義」一詞的歷史源頭,大概是說書傳統與章回小說,例如《三國演義》
漢語「忠義」一詞的歷史源頭,大概是說書傳統與章回小說,例如《三國演義》